從4月下旬開始,各路媒體記者雲集汶川、北川等地,他們開始準備5·12地震10周年的紀念報道。這註定是難以完成的任務,當初參加地震報道的記者,大部分已經改行瞭。新聞理想都抵不過歲月,有關地震的記憶,也很難抵擋。對新記者來說,如何“進入地震”,甚至都是一個問題。
10年,對宇宙來說不過一瞬,而對渺小的人來說,已經很長瞭。
2008年5月的媒體報道我曾經考察過一個抗日戰場。80年前,這裡炮火紛飛,中國軍隊為瞭阻擋日軍,不得不炸毀剛修建不久的一座橋梁。現在,那裡植被豐茂,和別的地方沒有什麼區別。僅有少數幸存者,可以指著那片土地講述當時的故事。
映秀震中附近,圖:黃新路在2008年,網上還很少看到視頻,一些“照片”凝固的瞬間,足以打動無數人。吳加芳騎著摩托車,背著死去的妻子,無數人就被這張照片打動瞭,尤其是女性,更為一個男人的有情有義所折服。地震後不久,就有一位女子找到吳加芳,宣稱愛上瞭他。他們很快就結婚瞭,又很快離婚瞭。
吳加芳成瞭一個大名人。一個月,一年,三年,媒體都會找他,檢視他“情義”是否還滿格。地震10周年報道,媒體還是忘不瞭他。他又有瞭愛情,經人介紹,他和一名女子相識並在一起瞭。但是,他當然不能忘記背上的妻子,他的願望,就是為自己的妻子立一塊碑。
5·12汶川大地震十周年:我們一邊忘記,一邊分離
朋友在群裡轉瞭一個叫“東辰小郎”的微博名片,我問:“這是誰?”郎錚,那個“敬禮娃娃”。我在腦海中搜尋很久,才想起這個人來。當初在廢墟中向解放軍叔叔敬禮的三歲娃娃,如今已經是翩翩少年,而當初拍下他照片的《綿陽晚報》記者楊衛華,卻已經不在人世瞭。
新註冊微博的郎錚,微博認證為“汶川地震敬禮男孩”。現在他才13歲,還不能體會什麼是時間。盡管很多媒體都大幅報道,在微博上關註他的仍然隻有兩千人——對不起,大傢已經忘瞭你。
汶川地震和唐山地震,都造成瞭很大的傷亡。但是唐山地震的時候,媒體和社會都極不發達。盡管在河南的村莊,也會有村幹部喊大傢睡到外面“躲地震”,普通人對發生在唐山的事情,仍然知之甚少。到瞭2008年,都市報正處於自己的頂點,每個省會的報紙,都有能力往災區派出記者。央視和四川衛視都進行瞭長時間的播報,有些救援還進行瞭直播。門戶網站也處在高速成長期,全國的上班族,都可以在辦公室第一時間刷新來自地震災區的新聞。
這就是很多人紀念地震的本質:我們需要的是故事,是情懷,而不是真相和解決困難。我們需要吳加芳一遍遍給我們講“想給妻子立一塊碑”,我們需要那一刻的感動。車隊監控系統更多的時候,我們不知道吳加芳是誰。除非你把當時的照片打印出來,旁邊寫著他的事跡,否則沒人會記得他。
幸運的是,“5·12汶川大地震地震”才過去10年,不管是媒體還是個人,還能用手指向那裡,還知道哪兒埋著最多的孩子。那些孩子永遠停止生長,他們的生平,讓人痛心。
就媒體的報道來看,這不是他最新的“願望”,而是一直以來的願望,前幾年就報道過瞭。妻子就葬在傢旁邊的地裡,立一塊碑,應該不是太難的事情。即便有困難,在媒體的幫助下,也很容易實現。但是,我們都沒有去實現這個“願望“,而是把這個願望一直懸置起來,在每一個時間節點拿出來講一遍,用來感動自己和別人。
2008年以來,社會變化日新月異,今天的我們,相互之間的聯系更方便、迅捷,但是,作為一個“社會”,我們卻以幾乎相同的速度分散開來。地震後形成的團結彌足珍貴,但是,如果它隻存在於地震後的一周,這種經驗又有什麼意義呢?
去年5·12的時候,企鵝問答曾經推出一個問題:“5·12地震時你正在做什麼?”結果,當天有幾萬人進行瞭回答。很多人來自北上廣這些遠離震區的地方,他們的記憶仍然清晰。不管他們是否有親戚朋友在災區,那天的2點28分,對他們來說都是有區分價值的“時間”。個體的記憶,也許並不是最真實、最可靠的,但是對每個人來說,這確實是最有價值的。
如果再大一點,他會懂得,“敬禮男孩”這個媒體貼給他的標簽,也許會成為束縛。5·12地震時媒體貼瞭很多標簽,試圖在悲傷的氣氛中,讓一些意義凝固下來。“敬禮男孩”、“抗震小英雄”、“地震背妻男”……但是10年過去,這些標簽早已一片狼藉。
大多數人為的標簽,都面臨著這種窘境。那個宣稱救出兩位同學的小英雄林浩,在8月的奧運會開幕式上,和姚明一起成為旗手。後來,開始有人質疑他造假。當時隻有9歲的林浩,媒體報道他的理想是到清華學建築,造出堅固的房子。後來,他成為瞭演員,但是在演藝事業也並不順利,如今的他,把自己定義為瞭公益人士。“小英雄”的光環和價值都在衰減,也許最終他不得不接受自己是普通人這個事實——這種結局,也許是最好的瞭。
有一位記者朋友向我講述一段當時的采訪經歷:地震三天後物流路徑規劃的一個傍晚,他們在帳篷外看到一個黑影在移動,走過去發現是一位老太太。她冒著危險,翻山出來求救。這樣的故事,現在看來是一個很感人的新聞,但是在當時卻並沒見諸報端,因為在當時這樣的“故事”太過普通瞭。
所以,後來“豬堅強”成為媒體聚焦的重點,很多人的求生故事,反而被冷落瞭,因為“豬堅強”足夠特別,可以貼上一個標簽。這很符合新聞學的規律,但卻讓人悵然:我們在追尋“意義”和“標簽”的時候,錯過多少鮮活有力的生命啊。
“豬堅強”我們該如何紀念地震?當初樹立的英雄人物,大多已經變成瞭凡人。其實,這是再正常不過的結局。時間奔流向前,沒有誰能夠永遠停留在原處。在時間面前,圖片和故事所貨車gps定位展示的“意義”,並沒有我們想象得那麼牢固。毫無疑問,這是讓人氣餒的。很多人在地震後發出的誓言,也和這些“意義”一樣歸入塵土。
如今那些在汶川、北川追尋“意義”的記者,很多都陷入瞭困境。重建非常成功,很多地震後建的學校,美麗而堅固。有些地震遺址,建成瞭博物館。我們總是想總結出整體性的“意義”,但是在“日常”的生活中,去紀念作為大災難的地震,總是困難的,有時候還是假惺惺的。
從根本上來說,地震造成的傷痛,總是個人的,大多數時候難以言說。在北川,清明節是最讓人動容的日子,而不逢是5·12當天的周年紀念。重建道路、學校、醫院總是容易的,而人內心的重建則無比艱難。清明節的祭奠更為動人,是因為這是活著的人與死者之間的橋梁。每一個活著的人,在為遇難者撒上紙錢的時候,他必然認識到自己的活著是一種幸運。在這樣的時刻,生和死才能達成某種妥協。
等冷靜下來,人們發現吳加芳其實是一個普通的男子。或許他背起妻子遺體的時候,心中充滿柔情。但是在漫長的日子裡,他終究是一個充滿缺點的男人。
運送救災物資途中,圖:黃新路最終,我們能夠講出的,仍然隻是自己的故事和經歷。它是鮮活的,因為我們還活著,會在內心的某一個角落,存儲下地震的記憶,且設置為永遠不能刪除。如果說媒體建構出來的意義很容易消散的話,我們在自己生命中刻下的印記,也許會更長久。我們的人生、愛情乃至命運,都有可能被地震所改變。
這種個人性的回憶與紀念,當然是有價值的,但是本質上來又總會顯得膚淺。我們是活下來的人,僅僅這一點,就可能讓我們感到僥幸,甚至內疚。那些在地震中遇難的人,如果地下有知,他們會如何看待我們的表演呢。
我們沉醉在個體的敘事之中,有時候甚至會忘記地震曾經讓我們團結起來,成為一個臨時的“共同體”。
地震造成的傷痛,總是個人的,大多數時候難以言說。在北川,清明節是最讓人動容的日子,而不逢是5·12當天的周年紀念。
這就是時間。
【責任編輯:肖肖】
show
- 車輛即時監控|gps車輛監控系統 豪美科技想要找GPS車輛監控系統~有推薦的廠商嗎?
- 豪美科技X戰警GPS車隊管理系統|車隊監控系統|gps車隊監控系統|車隊管理平台|gps車隊管理平台|車隊管理app 豪美科技有沒有汽車遠端監控系統?有人有用過嗎?
- 拖板車衛星監控系統|拖板車車隊管理系統 遊覽車專用衛星車隊管理|遊覽車專用gps車隊管理該如何找呢?
全站熱搜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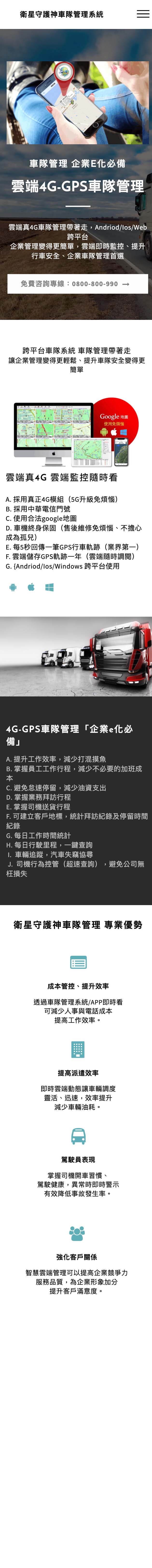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

